古人对饮茶用水的认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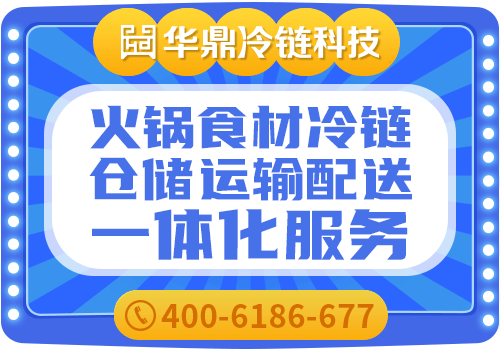
水,是茶的载体;离开水,所谓茶色、茶香、茶味便无从体现。因此,择水理所当然地成为饮茶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明代熊明遇《罗芥茶记》云:“烹茶,水之功居大。”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说:“茶性必发于水。八分之茶,遇水十分,茶亦十分矣;八分之水,试茶十分,茶只八分耳!”两段话,讲的都是一个意思:用好水泡较次的茶,茶性会借水而充分显现出来,变成好茶;反之,用较次的水泡好茶,茶便变得平庸了。
水在茶艺中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,因此,从唐代中期艺术性饮茶蔚成风气以来,择水、论水、评水,便成为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。归纳起来,历代论水的主要标准不外乎二个方面:水质和水味。水质要求清、活、轻,而水味则要求甘与冽(清冷)。
清,是对浊而言。用水应当质地洁净,这是生活中的常识,烹茶用水尤应澄沏无垢,“清明不淆”。为了获取清洁的水,除注意选择水泉外,占人还创造很多澄水、养水的方法,田艺衡《煮泉小品》说:“移水取石子置瓶中,虽养其味,亦可澄水,令之不淆。”“择水中洁净白石,带泉煮之,尤妙,尤妙!”这种以石养水法,其中还含有一种审美情趣。另外,常用的还有灶心土净水法。罗庚《茶解》说:“大瓷瓮满贮,投伏龙肝一块——即灶中心干士也——乘热投之”。有人认为,经这样处理的水还可防水虫孳生。
苏东坡有一首《汲江水煎茶》诗,前四句是:“活水还须活火烹,自临钓石汲深情。人瓢贮月归春瓮,小杓分江入夜铛。”南宋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评日:“此诗奇甚!茶非活水,则不能发其鲜馥,东坡深知此理矣!”
水虽贵活,但瀑布、湍流一类“气盛而脉涌”、缺乏中和淳厚之气的“过激水”,古人亦认为与主静的茶旨不合。用这种水去酿酒也许更合适。
水之轻、重,有点类似今人所说的软水、硬水。硬水中含有较多的钙、镁离子和铁盐等矿物质。能增加水的重量。用硬水泡茶,对茶汤的色香味确有负面影响。清人因此而以水的轻、重来鉴别水质的优劣并作为评水的标准。
据陆以恬《冷庐杂识》所记,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一个精工制作的银质小方斗,命侍从“精量各地泉水”。结果是:京师玉泉之水,斗重一两;济南珍珠泉,一两二厘;惠山、虎跑,各比玉泉重四厘……因此,乾隆还亲自撰文,把颐和园西玉泉山水定为“天下第一泉”。从此,出巡时必以玉泉水随行,但由于“经时稍久,舟车颠簸,色味或不免有变”,所以还发明了“以水洗水”的方法:把玉泉水纳入大容器中,做上记号,再倾入其他泉水加以搅动,待静止后,“他水质重则下沉,玉泉体轻故上浮,提而盛之,不差锱铢”。(据《清稗类钞》)乾隆测水、洗水的办法是否科学、可靠,姑且置而不论,但古人对“轻水”之重视程度,于此可见。
甘洌,也称甘冷、甘香。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谓:“水以清、轻、甘、洁为美,轻、甘乃水之自然,独为难得。”明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亦说:“凡水泉不甘,能损茶味。”水味有甘甜、苦涩之别,一般人均能体味。“农夫山泉有点甜”,这一时髦的广告语,倒也道出好水的特点。
明田艺衡说:“泉不难于清,而难于寒。”泉而能冽,证明该泉系从地表之深层沁出,所以水质特好。这样的冽泉,与“岩奥阴积而寒者”有本质的不同,后者大多是潴留在阴暗山潭中的“死水”,经常饮用,对人不利。而被称为“天泉”的雪水,却甚宜于烹茶。《红楼梦》中妙玉用藏了五年、从梅花上扫下来的雪水烹茗,虽然是小说家言,却并非全出于想象,经现代科学检测,雪水中重水含量比普通水要少得多,而重水对所有生物的生长过程都有抑制作用。
从水的质和味上加以长期观察后,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写下了“山水上,江山中,井水下”的结论。据唐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所说,陆羽还把天下的水分为二十等,依次列为:“庐山康王谷水帘水,第一;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,第二……”但与他同时另一位“为学精博,颇有风鉴”的刘伯刍却认为“扬子江南零水,第一;无锡惠山寺石水,第二……”排列次序大不相同。此后,关于各地水质次第的争论,竟延续了千年之久且一直未有结论。这说明了,感官鉴定难免有主观性和片面性。在鉴定水质方面要想做到既可意会,又能言传的话,还须靠科学分析手段。
目前,茶界对饮茶用水所认定的水质主要标准是:色度不超过15度,无异色;浑浊度小于5度;无异臭异味,不含有肉眼可见物;PH值为6.5~8.5,总硬度不高于25度;毒理学及细菌指标合格。
古人饮茶,注重于水自汲、茶自煎。把汲水、养水当成整个品茶过程的一部分。他们那些经过长期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品水结论,虽然带有一些玄虚的成分,但更多的是与科学道理暗合或相通。对此,我们既无须一味盲从,但也不应一笔抹煞。了解、掌握一些水须“清、轻、活、甘、冽”的原则,无疑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地选择饮茶用水。
水土相宜茶自佳由于条件所限,陆羽不可能遍尝全国各地名泉,所以能够荣列他的“名泉榜”的泉水(含雪水)只有二十位。但陆羽的名气太大了,以致历代不少茶人都囿守在这一“名泉效应”圈中而难于自拔。
晚唐的李德裕当宰相时,因喜爱惠山泉,叫人从江苏无锡直到长安设“递铺”专门为他运送惠泉水,自授政敌以攻击之把柄。北宋京城开封的达官贵人也极力推崇惠山泉,同样不远千里,运送惠泉水。欧阳修请蔡襄为他书写《集古录》序文,后精选四件礼品作为润笔,其中就有惠山泉一瓶。由于经过长途跋涉后水味易变,京师的茶客们还创造了一种“拆洗惠山泉”的办法:当泉水到达时,“用细沙淋过(即用细沙过滤一下,以除杂味),则如新汲时。”(周辉《清波杂志》卷四)明代讲究品茶的文人无法得到惠山泉,便挖空心思,把一般的泉水煮开后,倒入安放在庭院背阴处的水缸内,到月色皎洁的晚上揭去缸盖,让泉水承夜露,反复三次,再将泉水轻舀人瓷坛中,据说用这样的水“烹茶,与惠泉无异”,故称为“自制惠山泉”(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)。崇拜名泉至此地步,已有点“望梅止渴”的意味了。
其实,张又新的《煎茶水记》早已记录了陆羽的几句话:“夫茶烹于所产处,无不佳也,盖水土之宜。离其处,水功其半。”意思说:“茶出产在那里就用那里的水来烹煎,没有效果不好的,这是因为水土相宜。水再好,运到远处,它的功能只剩一半。
宋代的唐庚是个豁达者,他在《斗茶记》中说:“吾闻茶不问团铐,要之贵新;水不问江井,要之贵活。千里致水,真伪固不可知,就令识真,已非活水。”所以他被贬惠州时,每次烹茶,“提瓶走龙塘无数十步,此水宜茶,昔人以为不减清远峡”,旋汲旋烹,深得其乐。他曾作诗《嘲陆羽》,但从上述的几句话看来,他正是对陆羽的择水理论有深切体会的异代知音。
陆羽足迹未及潮郡,潮境内的泉水自然无缘进入“名泉录”,但这并不意味着潮境无好泉,潮人不晓择水。北宋唐庚《梦泉诗序》云:“潮阳尉郑太玉梦至泉侧,饮之甚甘,明日得之东山上,因作《梦泉记》示余,余作此诗。”诗中且有“名酒觉殊胜,宜茶定常煎”之句。又,《海阳县志·金石略》记潮州西湖山《濮邸题名》:“淳熙丙午中秋……登卓玉,上深秀,汲泉瀹茗,步月而归。”此皆宋代与潮郡有关的择泉记载。潮州的名泉,比比皆是:
潮州西湖的风栖泉、处女泉;潮安石庵的山泉、桑浦山的甘露泉;汕头舵浦的龙泉;澄海之凤泉、狮泉、象泉、灵泉、玉泉;惠来的甘泉、君子泉;潮阳的卓锡泉;普宁马嘶岩的流泉:揭阳的狮子泉、茉莉泉、八功德水泉……这里所开列的,是名副其实的“挂一漏万”,真要作一番普查的话,正不知要开出多长的一串名单。何况,还有很多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深山大岭中的“未名”泉!
除了山泉,潮境内的韩江、榕江、练江、凤江等等,只要未受污染,亦皆是水质纯美的江河。从前,沿江居民多有入江心取水烹茶者,有时江水稍浑,亦不用加什么白石、伏龙肝或施于“拆洗”手段,只须投入一点明矾,搅动几下,静置片刻便成清甘澄碧的好水,其味不下山泉。
此外,遍布城乡的水井,亦是红茶业工夫茶客最方便而且取之不竭的烹茗源泉。在幽静的古城中,每家都有一口以上大小不一的水井,有客登门,几句寒暄之后,马上开炉升火,再亲临井边,抖动长绳短绠,颤悠悠地汲起一小桶夏冽冬温的井水来。望着水面摇漾不停的波光,听着那淅淅沥沥的滴水声响,自有一番舒心的意趣。
当然,显着名且屡成名家吟咏对象的,还是潮州湖山的山泉。丘逢甲《潮州春思》之六,至今仍脍炙人口:
曲院春风啜茗天,竹炉榄炭手亲煎。
小砂壶瀹新鹪嘴,来试湖山处女泉。
饶锷先生《西湖山志》谓此泉“深居幽谷,从不见人,正如处女,故以处女名之。时有游虾逐队而出,泉活故也。”因此,昔时潮城中有陆羽癖者,皆往彼处汲取活泉,甚至有专以挑运泉水为生者。相传有一富家日日雇人挑水,每当泉水进门,只取前桶而倾去后桶之水,人问其故,曰:“后桶多汗气、屁气。”这则传说很快会使人联想起元代大画家倪云林的一段趣事。据《驹阴冗记》所载:云林“尝使童子入山担七宝泉,以前桶煎茶,后桶濯足。人不解其意,或问之,曰‘前者无触,故用煎茶:后者或为泄气所秽,故以为濯足之用。’”上述两家,确实迂腐得可以。试想入山挑水,哪有中途不换肩的道理?路愈远,换肩的次数愈多,两个水桶,又怎能分清哪个为前,哪个为后?不亲事劳作的人,难免要闹出一些常识性的笑话。不过,不管传说是否属实,在慎于择水这一点上,的确是古今茶人,人同此心。

标签:
上一篇:古人对饮茶用水的认识
下一篇:返回列表

 酒业新闻
酒业新闻 茶业新闻
茶业新闻 食品新闻
食品新闻 酒知识
酒知识 茶知识
茶知识 行业展会
行业展会 茶道文化
茶道文化 茶艺
茶艺 网站首页
网站首页